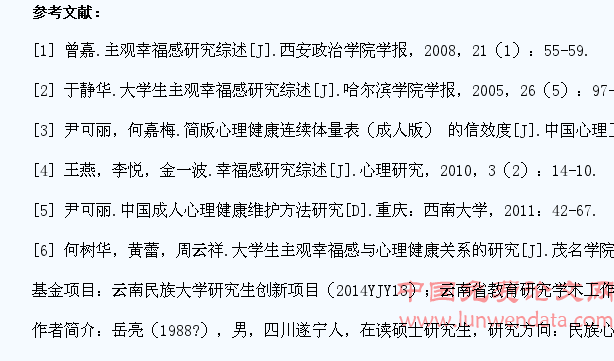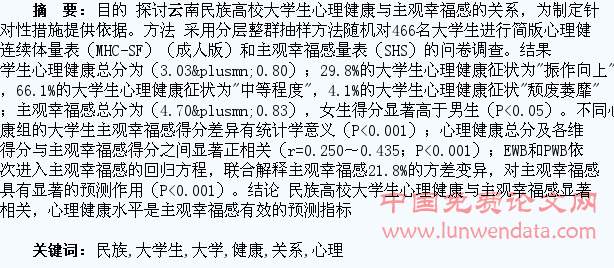摘要:目的 探讨云南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随机对466名大学生进行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MHC-SF)(成人版)和主观幸福感量表(SHS)的问卷调查。结果 大学生心理健康总分为(3.03±0.80);29.8%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征状为“振作向上”,66.1%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征状为“中等程度”,4.1%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征状“颓废萎靡”;主观幸福感总分为(4.70±0.83),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5)。主观幸福感总分为(4.70±0.83),其中汉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为(4.74±0.81),少数民族大学生为(4.65±0.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生主观幸福感总分为(4.60±0.88),女生(4.80±0.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82,P
2、不同心理健康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表1) 大学生颓废萎靡、中等程度、振作向上3组在主观幸福感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颓废萎靡组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的得分显著低于振作向上和中等程度组的大学生(P
4、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预测力回归分析(表3) 以主观幸福感得分为因变量,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EWB和PWB依次进入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方程,联合解释主观幸福感21.8%的方差变异,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三、讨论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心理健康不仅是没有心理疾病,还应该包含一些积极的方面。目前,心理健康没有统一的测量和诊断标准,国内学者心理健康的研究较多采用SCL-90量表。SCL-90量表主要偏向测量消极的心理疾病症状,重点用于鉴别临床症状,对正常人或精神病理症状较少者适用性较差[5]。鉴于此,本文采用适用性更好的MHC-SF量表。研究结果表明,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均值为(3.03±0.80),心理健康征状为“振作向上”的比例仅为29.8%,说明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高校和政府管理部门应给予大学生群体更多的关注,引导和帮助他们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Lyubomirsky和Lepper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虽然不是目前应用最普遍的测量幸福感的量表,但被证明对于跨文化群体的测量具有很好的适用性[4]。研究发现,民族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为(4.70±0.83),处于中等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民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受到民族差异的影响,性别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子,女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因此民族高校管理部门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对于男同学群体应给与更多的关注。
研究发现,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主观幸福感得分之间显著正相,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且颓废萎靡组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的得分显著低于振作向上和中等程度组的大学生,表明心理健康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因素。回归分析发现,EWB和PWB依次进入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方程,联合解释主观幸福感21.8%的方差变异,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与何树华[6]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民族高校大学生情绪性安康和心理性安康是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因此,提高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内容,而提高情绪性安康和心理性安康水平是重点。